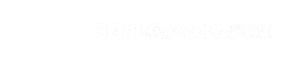从争议解决视角看主从合同涉外因素的认定及管辖条款的设计
2025.09.26 祁达 李岳明
一、引言
随着国际商事交易复杂性的不断提高,各方当事人的合作模式往往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合同或协议确定。主从合同是关联合同的一种典型类型,通常由能够独立存在的主合同及效力依附于主合同的从合同构成。狭义上,从合同仅指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的从合同类型,即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保证合同。而广义上,除法律明确规定外,从合同还可以通过当事人通过明确约定的方式创设的从合同,例如保修合同。
在关联合同起草和订立的过程中,管辖权条款往往是境内外企业博弈的关键战场。然而,民事法律关系具有涉外性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管辖机构的先决条件。如果合同所涉法律关系整体或部分被认定为不具有涉外性,相关合同主体将可能丧失将案件提交至外国法院或仲裁机构管辖的权利。
在单一合同纠纷中,涉外性的判断相对直观:只要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系争标的物)或内容(产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事实)中任意一项存在涉外因素,该案件一般即会被认定为具有涉外性。反之,如果合同的签订主体均为国内企业、签订地点在中国境内且合同主要权利义务在中国境内履行,除非一些特殊情况1,法院一般会倾向于否定案件的涉外性。本文将结合中国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探讨主从关联合同的涉外性认定问题,以及在相关合同条款的谈判和设计中的注意要点,以期为读者提供参考。
二、司法实践中对主从合同的涉外性认定
(一)主合同具有涉外因素,从合同本身没有其他涉外因素
常见的模型是境内外主体之间签订基础合同,并由境内主体提供担保。此时,由于担保合同具有从属性的特征,法院有可能认为境内主体之间的纠纷具有涉外因素。
在(2019)冀民申9466号案件中,境内债权人A公司与境外债务人B公司签订主合同,中国公民江某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后A公司仅起诉江某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认为本案不具有涉外因素,但河北高院经审理认为:“主合同为涉外商事合同,担保合同即符合“对外担保”的特征要求,二审法院认为应当按涉外民事案件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在(2020)京民辖终69号案件中,利比亚国家住房部与境内债务人A公司签订《5000套利比亚居民福利住房项目总承包合同》,为担保这一债权,北京某银行为A公司开具两份预付款反担保函,A公司为此提供了一系列担保。A公司在北京法院起诉某银行,主张因预付款反担保函已经到期并终止,且在其有效期内未产生任何债权债务,故要求某银行解除涉案系列担保合同项下的抵押权和质押权。北京高院经审理认为:“鉴于预付款反担保函系某银行向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开具,且该反担保函项下建设项目位于利比亚,预付款反担保函有效期内是否产生债务,直接取决于利比亚撒哈拉银行是否实施主张权利等法律行为,故导致涉案担保法律关系消灭的法律事实,与外国法人利比亚撒哈拉银行是否要求展期、提出索赔等事实紧密相关,且主要发生在我国领域外,因此,涉案担保法律关系内容具有涉外因素”。
在(2016)浙民终922号案件中,A公司与B公司(均为境内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涉及在利比里亚的重油电站工程建设。义乌某银行应B公司申请,开具了受益人为A公司的预付款保函。后义乌某银行提起诉讼,认为A公司和B公司共同构成保函欺诈。二审中,A公司主张本案无涉外因素,浙江高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保函对应的基础合同涉及在我国境外的重油电站工程建设,一审法院认为该保函服务于国际商事交易,具有涉外因素并无不当。”
这就意味着,在主合同被认定具有涉外性的情况下(如主合同当事方存在涉外主体、合同标的物或履行地点在境外等),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25修订)》的规定,当事人均可以在主合同和从合同中自由约定域外管辖条款;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的规定,即使主合同与中国无任何实际联系,当事人也可以约定由中国法院管辖。同时,依《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2022年实施)》之相关规定,若当事人在主从合同中约定由不同国家或地区法院管辖,或分别约定诉讼和仲裁两种不同争议解决方式,此时法院将依据主、从合同的约定分别确定管辖。
(二)主合同不具有涉外因素,从合同具有涉外因素
常见的模型是境内主体之间签订基础合同,并由境外主体提供担保。此时,法院对案件涉外性的认定存在以下情况:
在(2018)最高法民终168号案件中,最高院认为:“借款合同当事方A公司与B公司均为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借款合同不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王某系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王某为保证人的《自然人保证合同》为涉外担保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自然人保证合同》的当事方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该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是与本案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故本案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解决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
在(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S320号案件中,A、B中心均为境内公司,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合作建设、管理和运营水疗项目。合同中约定有保证条款,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某(印度尼西亚国籍)在合同上签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A公司同时起诉B公司和王某某承担责任,上海一中院认为:“本案主合同为A中心与B公司之间的联营合同,不具涉外因素,故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正确。另外,A中心依据《合作协议》中担保条款要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籍当事人王某某承担担保责任,故该担保合同关系具有涉外因素,鉴于三方当事人在《合作协议》中约定适用中国法律,故本院予以确认”。
在(2012)民四他字第2号案件中,A公司(境内)与B公司(境内)签订了风力发电机叶片的《贸易协议》。该协议附件C约定了丹麦B公司对预付款的担保责任,担保关系适用丹麦法律;附件D约定了丹麦B公司的保修责任;附件E约定了西班牙某公司的担保责任,担保关系适用西班牙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答复意见中认为:“尽管A公司与B公司间签订的《贸易协议》不仅涉及双方当事人之间买卖风力发电机叶片,还涉及各自母公司即外国法人的担保及保修责任,但由于担保及保修相对于风力发电机叶片买卖关系来说为相对独立的合同关系,故其并不影响《贸易协议》中买卖风力发电机叶片为国内民事关系的性质。”
在(2013)虎民辖初字第0004号案件中,A公司与B公司(均为中国法人)签订《企业间合伙协议》,该协议争议解决条款约定,将争端提交国际商会巴黎仲裁机构。合同第九项约定,A公司提供150万元银行担保,由A公司出具德国银行的担保证明。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法人,诉讼标的物在中国境内,所涉合同签订、履行等法律事实均发生在中国。双方协议中虽有一条款约定一方当事人负有出具德国银行担保证明的义务,但是本案并非因该担保产生的纠纷,因此,本案所涉纠纷不具有涉外因素。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将不具有涉外因素的争议交由境外仲裁机构仲裁,故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将没有涉外因素的争议提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仲裁没有法律依据,应认定本案仲裁协议无效。”
从上述案例中可见,商事主体在签订关联合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构造”关联合同的涉外因素,从而使得发生争议时一方可以将合同纠纷整体提交至外国法院或仲裁机构并适用外国法律解决的目的。类似的尝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认定事实和理由不一而足。
三、一体两面: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的涉外因素设计与考虑
在跨境商事合同的起草过程中,由于合同当事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对于跨境合同管辖的争夺往往会成为双方在谈判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在特定情况下,管辖条款的争夺和设计,甚至可以左右一方最终是否愿意提起法律程序(例如,在国外诉讼或者仲裁情况下引发的高昂法律费用和漫长时间成本考虑)。因此,是否能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去有效“制造”合理的涉外因素,可能会是合同双方关注的焦点。结合以上案例,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往往因忽视或错误判断主从合同关系在未来诉讼中的涉外性认定问题而导致前期多番谈判订立的管辖条款无法实现预期的目的。基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涉外案件管辖认定相较于普通国内案件更为复杂,除管辖条款约定的内容外,当事人采取不同的签订形式、起诉方式以及从合同本身的性质等因素均可能对最终管辖条款的适用产生影响,我们试简单列举可能存在的不同情况(非穷尽):
涉外因素 | 签订方式 | 管辖权约定方式 |
主合同具有涉外因素,从合同本身不具有其他涉外因素 | 合并签订或分别签订但管辖权约定一致 | 1) 域外管辖 |
2) 中国法院管辖 | ||
分别签订且管辖约定不一致 | 1) 主合同约定域外管辖,从合同约定中国法院管辖 | |
2) 主合同未约定,从合同约定域外管辖 | ||
3) 从合同未约定,主合同约定中国法院管辖 | ||
主合同不具有涉外因素,从合同具有一定涉外因素 | 合并签订或分别签订但管辖权约定一致 | 1) 域外管辖 |
2) 中国法院管辖 | ||
分别签订且管辖权约定不一致 | 1) 主合同约定中国法院管辖,从合同约定域外管辖 | |
2) 主合同约定域外管辖,从合同未约定 | ||
3) 从合同约定域外法院管辖,主合同未约定 |
由上表归纳可见,合同双方在起草和谈判主从关联合同管辖权条款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首先,按照涉外因素三要件(也即民事关系主体、系争标的物、设立、变更或终止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判断主合同的涉外性,如果主合同具有涉外因素,即便从合同签订各方均为国内主体且签订地点为中国,在其未明确约定由中国法院管辖的情况下,中国当事人依从合同提起的纠纷仍存在提交域外审理或仲裁的可能空间。此外,在约定管辖过程中还须注意涉外因素认定的一些特殊规则(例如,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
2、其次,判断从合同的性质(例如,是否是担保责任类型还是其他类型的从合同)。鉴于不同性质的从合同可能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须谨慎评估从合同的属性,对于复杂的跨境合同而言,从合同也可能包含多项权利义务,如何设计相关的从合同权利义务也需要相应予以考虑。
3、如果主合同不具有涉外因素,将主从合同合并签署且约定域外管辖可能会存在问题,此时若合同签署方希望将从合同纠纷单独提交域外管辖,则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签署合同的方式。
4、此外,在复杂的跨境商业合同中,还有可能会涉及多个不同商事主体及其境外关联公司之间的主从合同关系,合同的实际履行,对于是否发生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涉外因素”,以及是否由此产生涉外管辖的基础,需要在主从合同执行过程中特别予以关注。
四、结语
跨境商事合同中的涉外因素设计,往往会对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效力产生直接影响,对于交易双方而言不容忽视。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当今市场环境下,有些公司即便在交易中吃了大亏,也鲜有在境外启动法律程序的勇气(以及成本和精力),宁可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甚至连前期评估和准备的工作都放弃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忽略了对合同争议解决条款的博弈所造成的。
再从另外一个视角而言,回归到法律服务的本质,交易律师也应当了解争议解决的门道,才能更好的起草合同条款,从而真正帮助客户在未来的争议中立于不败之地,防患于未然。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好的条款设计,在争议发生前能够威慑对方,从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真的引发争议,届时也能更好保障已方权益,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尽管相当一部分的跨境商事合同未必最终会走到争议阶段,走到争议阶段也可能最终以和解方式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合同条款起草的好坏没有区别,因本着审慎之心充分评估商事合同中的各项条款,谋而后定,定而后动,先胜后战,一战而胜,避免发生争议后再去“险中求胜”,这也是笔者所认同的争议解决之道。
声 明
《君合法律评论》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得视为君合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该等文章的任何内容,请注明出处。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转载或使用该等文章中包含的任何图片或影像。如您有意就相关议题进一步交流或探讨,欢迎与本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