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合35丨我在君合这20年
2024.11.16 谢青
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
今年三月初的一天,结束了在开曼群岛M a p l e s律所Investment Fund Conference后,我在迈阿密转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望向脚下的万家灯火,一时思绪万千。记得十二年前的这个时候,在纽约逗留一周拜访客户后,我独自从纽约飞往迈阿密参加在Boca举行的FIA(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年度会议。我第一次出国参加非律师组织的行业盛会,FIA可能也是首次迎来中国大陆的律师代表。那会儿我还没有资格作为嘉宾发言而只是参会,到处换换名片。老外的networking event特别适合E人,不管多陌生都可以立刻像老朋友一样端着个酒杯或餐盘站着开聊。任凭你是MD还是CEO,也都是站着的份。除了我这个中国面孔外,还有来自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参会代表,大家辛辛苦苦飞越半个地球去参会,就是为了向老外宣传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
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由于发现国际会议是获客的绝佳场合,我在国际会议上投入的精力和热情一直不减,持续宣传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监管政策。市场好就谈开放,市场不好就谈监管,话题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起伏而变化。除了疫情三年不得已改为线上参加,我每年都要出境几次参加知名的期货或基金行业会议,不是作为分论坛的嘉宾,就是作为主持人,成了涉外期货和证券基金行业的熟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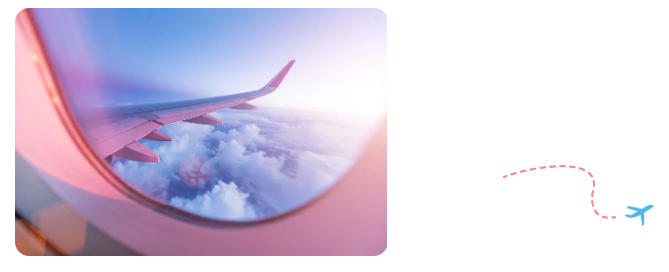
我曾经的业务领域很杂,在1999年到2009年执业第一个十年,涉猎公司并购、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合规、银行贷款业务。各类业务需要的律师个性特点不太一样,有些律师有商业头脑,是deal maker,像周辉律师;有些律师功底扎实,特别擅长文件制作,像姚建波律师(现为汇丰银行中国首席法律顾问);有些律师因为细致周到受到inhouse lawyer的普遍欢迎,像何侃律师。我赞赏那些有商业头脑的合伙人,也佩服可以没日没夜和客户以及交易对手耗体力的交易律师。我自己的精力有限,不能熬夜,性格也比较保守,厌恶风险,但我的优点是有亲和力,有耐心在同一领域深耕。因此,以期货衍生品和私募证券基金为特色,以金融机构客户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为基础,建基于金融监管的业务领域,比较适合我。陪伴客户成长并与客户建立更深层次的相互认可及合作关系,符合我这种“长情”“专一”、不吝长期投入的性格。
从业十年后,我半主动半被动转换专业赛道,2010年和2013年,因缘际会,我分别进入商品期货和私募证券基金法律服务领域,终日与对冲基金等各类境外投资机构客户为伍,形成了自己的专业特色。这一非常小众的领域带给我众多境外机构客户的广泛认可,让我至今非常感激和惦念当年的“引路人”和陪伴我一路走来的合伙人们。
潘跃新律师就是我的引路人之一。时针拨回到2010年的某一天,潘跃新律师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他嘉里中心25楼的办公室,说有个中外合资期货公司在挑选律师,问我有没有兴趣,具体情况得见了客户再说。我和潘律师本来没有太多交集,但我一直仰慕潘律师的潇洒风度和随和豁达。他一招呼我,我欣然应邀前往,去见了他引见的这家期货公司的中外方代表,见完后我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我不但能帮助这家期货公司解决其客户的法律问题,而且我发现有很大机会通过这家期货公司开发更多老外客户。潘律师一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架势,完全放手让我去做,案源滚滚而来。唯一遗憾的是潘律师后来也转换赛道,不做律师了,如果他还在做律师,凭着他的资历和熟人网络,说不定还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商机”。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合伙人们不但是我的“引路人”,还见证了我的成长。时针再次拨回到2013年的某一天,我在嘉里中心32楼拐角的办公室。刚刚生完二宝休完产假的我很兴奋,指着桌上摊开的刚刚生效不久的证券基金法和刚刚发布的私募基金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对经常一起合作的合伙人程虹律师和董剑萍律师感叹,感谢立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给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业务机会!从期货到私募证券基金,这两个领域有很多共通之处,凭借之前的客户和经验积累,我们只要持续努力,一定能在外资私募证券领域复制在期货法律服务市场的成功。当时她俩都特别感动于我的工作热情,在此之后也以实际行动兑现她们承诺的支持。记得当时董剑萍律师还感慨说,其实这个成功并不容易复制,因为这样一个小众且前沿的业务领域需要我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不断追踪市场发展,一家家与客户沟通,一刻都不能停歇。
在此之前的2012年年初,我就已经在纽约见了几家大名鼎鼎的量化对冲基金巨头。当时除了得到纽约办公室同事们的热情接待外,北京办公室的周军律师正巧在美国,她一听我提起这么新的业务领域,顿觉有趣,欣然决定陪着我奔波在寒风凛凛的纽约大街上,一家一家拜访客户。几次客户会议后,周军律师开玩笑说她都快背会了我给对冲基金客户精心准备的那一篇推广“话术”。
以前常听说“文人相轻”,但很显然这话不太适用于律师行业。这个行业的专业性决定了不同专业律师之间为了开发和维系客户必须少内耗、多协作,互相支持,积极合作。共同的背景经历和成长环境有助于这种平等的合作。君合的好几位合伙人都曾是我的同学或者校友,比如程虹律师。我们同一年毕业,毕业后成家前一起租房合住。此后,我们各自跟随一位带我们入行并且对我们的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律师前辈,说来也巧,我们俩的老师的英文名都叫David Liu。我们也是先后结婚生子,有美满的家庭生活,也先后决定要了二宝,不时沉浸在为人母的喜悦中。我们俩在各自生二宝的怀孕和生产时期更是互为后援。我俩有一家共同服务的以色列客户,只信任我俩,客户如果见不到我,就一定要见Julie(程虹律师的英文名),只有我俩彼此可以相互取代。
平等的帮助不仅来自合伙人,还来自和我一起工作的业务律师和秘书,我们把彼此的性格都摸得和家人一样透。能干的业务律师极大地解决了合伙人的后顾之忧,可以让合伙人专心开发市场。秘书就像合伙人们的拐杖,离开了我的秘书,发账单和催账很多琐事会让我抓狂。
工作之余,性格爱好和习惯的差异也会给合作带来很多趣事。我的同事张弛律师比我小十三岁,记得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眼见着他的小脚裤下面露出一双颜色鲜艳的袜子,特别扎眼。古板的我对时尚不太拎得清,并不太懂得这种时髦,于是乎就忍不住在见完客户后建议他下次换一双深色的袜子,好几年后我才意识到是自己老土,自此之后再也不会建议他换袜子了。搞笑的是,他并不了解我的心路历程,一次我不小心瞄向他的袜子,他苦笑着说,这已经是我最后的倔强了,就请保留我这最后的倔强吧。

除了纽约和伦敦,香港对我而言可以算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开拓业务的城市。中环实在太方便,开会不用带包,下雨也不用带伞,一天能安排七八个会面。不管是在客户办公室,还是在楼下咖啡厅,都一样高效。还记得武雷律师带着我们这几个合规小分队成员去香港开拓市场,陈歆律师从上海飞来,郑艳丽律师从北京飞来,胡义锦律师从深圳坐地铁过来,大家一起在香港“扫楼”。而我们香港办公室所在地Jardine House因为位置绝佳,成为会见客户以及召开研讨会的大本营。在三十七楼的大会议室,我前后组织过十余场讲座,其中有一半都是给其他专业的同事“搭台唱戏”,包括陶旭东律师、吴曼律师、董潇律师、汤伟洋律师等等。可容纳40人的香港大会议室最多一次来了60多位客户,晚到的客户不得不站在墙角听完全场演讲。香港客户们的自觉性值得赞赏,大家都是静悄悄地签到,静悄悄地听完,有问题就问,不需要特别招待。放眼世界,大概只有香港能做到如此高效。
大所好似黄埔军校,人们来来去去,见证彼此的成长。同袍之谊是这些年最珍贵的回忆。如有幸坚守到最后,不但可以参加同事的婚礼、吃庆生的喜蛋喜糖,甚至有可能吃上同事孩子结婚的喜糖和抱孙子的喜蛋——可惜如今可能因为结婚率和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我们吃到的喜糖喜蛋变少了。还记得我女儿小时候最可爱的一张照片就是何侃律师在董剑萍律师的婚礼上抓拍的,我女儿是小花童,拎着新娘长长的礼服裙摆,新娘换一套衣服,她也要换一套衣服。
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合伙人之间如果没有利益纠葛,也不在乎虚名,就可以有更牢靠长久的友谊,有些还可以成为生命中的诤友。
李骐律师是我的师长一辈,他和我的老师刘大力都来自三十多年前上海专门从事涉外业务的三所。我以前做律师和工资合伙人的时候都尽量绕着李骐走,不被他看到。他会拿着业务律师写的英文memo叹气,叹到让律师们怀疑人生。后来他的性格因为信主而变得越来越谦卑顺服,想要批评业务律师的活计,拿起电话的头十分钟总要顾左右而言他,酝酿很久,怕言语伤着别人,让接电话的同事听着感觉他特别“绕”,大家不由私下里忍俊不禁地吐槽他,但也确实感觉他越来越谦卑顺服了,经常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他会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忘记刘大力律师的提携和知遇之恩,也会提醒我注意自己的脾气性格,不要对业务律师要求太严苛,这些诤言我至今谨记在心。
律师这个职业总是在拼谁的身体更好,谁能坚持得更长久,但也在考验谁能从工作中抽离出来,既享受工作带来的满足和成就感,又不为工作所累,不为欲望所控制,好好地享受生活。做到这一点其实挺难,因为身处其中,确实有点身不由己。每天从早忙到晚,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把身体的本钱搭进去。而且,人在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很少不骄傲。工作在消耗我们精力的同时也在对我们施加魔力,影响我们的性格和脾气。我也不例外,不小心就会把工作的态度带到家里,看似雷厉风行,杀伐决断,其实对家人的态度常常自以为是,颐指气使,还不小心就被成功冲昏了头脑,觉得成功就是因为自己努力,忽视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它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今年是我进君合第二十个年头。回首往事,萦绕心间的是充满喜乐的回忆。说起这么长律师的执业生涯,除了偶尔会有疲累,还真没有厌倦过工作。加入君合之前在上海的另外一家内资事务所工作了五年。这二十五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只有在相隔八年分别生下两个孩子前,因为身体实在无法应付繁重的工作,才全然放下工作享受了好几个月的悠闲假期。
进君合不久就参加了一次全所的出游。那次是在杭州,我和我先生,跟着很多后来成为合伙人的年轻同事们自发组织去西湖边的club看了一场夜场钢管舞。多年以后回忆起来,还记得同事们的欢声笑语和舞者的曼妙舞姿。第二天,我和先生租了两辆自行车绕湖骑行,天气风和日丽,我们的心也无忧无虑。那天居然吃了四顿正餐,只为了不错过杭州的美食。此后不久,在特别繁忙的工作间歇,上海办公室还组织了一次泰国的普吉岛之游。在导游的忽悠下,我们十几个人坐着快艇去一个叫帝王岛的小岛,路上突然遭遇风暴,乌云压顶,狂风暴雨,浪大风急,似乎要掀翻我们的小船。大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潘跃新律师和马建军律师带领大家一起喊起号子唱起歌,如此一路,平安返航,有惊无险。

进君合两年后我被擢升为工资制合伙人,得到消息的那天,我和先生还有两岁的女儿正和几位要好的同事和家人在苏州的太湖边游玩。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朋友们的祝贺胜过独自欢喜。只有我先生心里暗自为自己加油鼓劲,希望在收入方面还有机会能追上我——当然从此他是赤着脚也追不上了,这是后话。
此后每一年夏天的合伙人会议,我都很享受合伙人聚会的快乐时光。2007年夏天合伙人会议前夕的那一夜,在君合创始合伙人王之龙先生家的四合院里,众人聚在小屋里喝酒,男合伙人都赤膊光膀子喝白酒,我和李洁律师在院子厨房里给欧姨打下手。精力充沛、忙里忙外的欧姨,一碗碗喷香的炸酱面,就是家的感觉。
2010年,合伙人大会破天荒批准了十名工资转有限的转制申请。不得不说,2008金融危机推动了当年君合的转制。要不是金融危机,我还不知道要在工资制合伙人的位置上再多熬几年。得到好消息后,我们几个新晋合伙人一起去卡拉OK。麦霸佟珂律师本来应多多展现他美妙的歌喉,但迫于新晋合伙人们的激动和放飞,麦克风始终到不了他的手里。
2013年,直到许蓉蓉律师组织了一次北京和上海二组全体律师的出游,才刷新了我的认知,玩笑原来可以这么开,聚会原来可以这么嗨。武晓骥律师的幽默让人笑疼肚皮,而一丝不苟的马洪力律师居然也可以配合将聚会的气氛烘托到如斯地步。如果在其他事务所工作,考虑到合伙人们大多一丝不苟等级森严,肯定没有机会感受到像君合这种文化的可爱之处。
合伙人会议组织的旅游让我们感受到了“有组织关心”的快乐,完全没有包袱,也不用自己规划行程,总是好友相见分外开心,也总是能认识有趣的合伙人。阿拉善之行、青岛之行、林芝之行、成都之行、敦煌之行、日本之行、台湾之行、迪拜之行等等,君合合伙人大会会务组的世界级VIP服务,每一次都那么体贴周到,让人颇为怀念。
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我在君合的日子,匆忙而愉悦,我享受着工作带来的简单快乐。但从2013年开始,伴随着事业上一帆风顺,我也遭受了生活上的重大挑战。由于我先生患上了罕见难治的神经退行性病变,治疗康复无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生活得像两面人,在工作的时候状态良好精神抖擞,能打能拼,在家面对先生的时候绝望无助痛苦不堪,承认自己力有不逮,无法延缓他病情的发展,让他恢复活力。我艰难地平衡自己的心态并且咬牙坚持。百分之八十的时间我仍然花在了工作上,百分之二十的时间我又当爹又当妈陪伴两个相差八岁性格迥异的孩子成长。
回首往事,其实我那个时候很幸运,可以在我热爱的本职工作里消耗精力取得成绩储蓄能量,也可以躲藏在我的育儿工作里疗伤,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获得无限的满足感。最幸运的是,因为我在工作中已经和同事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我不怕坦承自己的软弱和无助,从不迟疑于求助。大到求医问药,小到教育孩子,从工作到生活的各种问题,我第一时间想到求助于君合的合伙人们,我知道我的同事们总是会慷慨相助,伸出援手。大连分所的李洁律师比我大十岁,一直为我收集海外最新的膳食补充剂和治疗信息,帮助我建立营养学和健康管理的理念,提醒我千万注意身体,还大老远来看望我先生,庆贺我和他成功延缓病情,创造了奇迹。她的鼓励和支持一直是我在困难时期的依靠。

一晃十年又过去了,我已经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我先生的病情比较稳定,我也处变不惊,疾病的进展和各种挑战不会再让我感觉如坠深渊。而且,我向合伙人们公开自己的艰难经历还不小心有个副产品,那就是在饭团群里建立了一个励志的形象:中午大家一起吃工作餐,彼此吐槽完工作和家庭后,比惨的同时想想我的处境,似乎觉得自己的那点困难不算什么,退一步海阔天空,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
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看,痛苦和忧虑并非无法解脱。患难促使我思考我所依靠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需要来自他人的帮助和支持。在一帆风顺的时候我要常常喜乐凡事感恩,遭遇困难也可以让我专心应对眼前的困难。如果在专心应对之后仍然克服不了这些困难,躺平并且重新审视自己的去处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