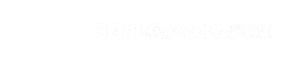学术会议及讲课费在《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规制下的存在空间及执法关注要点
一、引言
2024年10月1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仅三个月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终于2025年1月10日正式发布并实施《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下称“《指引》”)。
《指引》体现出国家监管层面的态度,从内容而言,为药品、医疗器械各领域所涉及的学术拜访交流、接待、咨询服务等典型场景提供操作指引,以注意事项给予正向引导、以风险识别与防范给予负向提醒1。随着《指引》的正式实施,其也将成为企业内部合规管理以及监管部门调查执法的依据之一。
二、各地合规指引陆续出台
实际上,医药行业领域的反腐工作长期以来都是执法的重点。2024年5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疾控局等十四部委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2024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卫医急函〔2024〕101号),明确“统筹开展、一并推进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深入协同推进医药购销领域制度建设”2。这一要求标志着自2023年掀起的医药行业反腐风暴在2024年将得到延续,并且相应监管标准也会日益明确。
在《指引》(包括其征求意见稿)出台以前,各地已经纷纷出台医药企业的合规指引。比如,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湖北省医药企业反商业贿赂行为合规管理指引(试行)》3、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重庆市医药领域反商业贿赂合规指引》4。此外,还有河南、山西、黑龙江省等省份也有相应的通知出台。上海市宝山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办公室、区司法局还牵头出台《上海市宝山区生物医药产业合规指引》,是上海首部生物医药产业的合规指引5。其中,学术会议、讲课费等行为,均是这些合规指引重点规制的内容。医药反腐领域逐渐形成了以国家政策性文件为纲要、地方性合规指引为细则的体系化规范标准,反腐工作更加深入。
三、学术会议及讲课费在《指引》中的存在空间
从《指引》内容来看,其肯定了咨询服务这一典型场景,即“医药企业聘请医疗卫生人员以其专业知识、经验和方法提供专业性指导,并向其支付合理报酬”。我们注意到,在《指引》征求意见稿中,咨询服务明确列明“授课、调研等”,但在正式版本中将“授课、调研等”予以删除;此外,《指引》征求意见稿中“建议医药企业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医疗卫生人员支付服务费”,在正式版本中调整为“建议医药企业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服务费”。上述变化,亦引发业界讨论,即《指引》是否延续《关于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工作提示的通知》对于学会会议召开主体、讲课费支付主体的精神。
而上文所提到的《关于医务人员学术讲课取酬工作提示的通知》,于2023年底开始在网上流传。该通知载明会议举办方和授课邀请方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医疗卫生机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社会组织”,措辞中并未有医药企业身影;同时,该通知亦严禁医务人员“直接接受医药行业相关企业给予的讲课费”。这一通知被广泛转载,引发解读认为医药企业不得召开学术会议、医生也不得收取讲课费。
结合我们处理调查案件的经验而言,我们尚未关注到执法部门对于医药企业举办学会会议、支付讲课费的直接否认,其更多还是从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角度来进行调查。根据公开媒体报道6,某知名医药企业因其子公司邀请医生参加学术活动并给予劳务费,被某地市监局于2024年予以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超2000余万元、罚款200余万元。另外,根据公开报道7,在2024年6月13日,某地市监局亦对另一家医药企业支付讲课费行为进行处罚,所涉罚款为6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超300万元。这些报道中医药企业被行政处罚,还是因为存在违规造假,而非因身份问题不得召开学会会议、支付讲课费所导致。
我们亦倾向于认为,医药企业举办学术会议、支付讲课费,符合“医疗卫生人员以其专业知识、经验和方法提供专业性指导”,即属于咨询服务范畴,并非被禁止,且需要满足下述正向引导、负向提醒要求:
/ | 正向引导 | 负向提醒 |
目的 | 真实、合理、合法的业务需求 | 禁止以咨询服务名义输送不当利益 禁止奖励、诱导医疗卫生人员开具医药产品处方或者推荐、宣传、采购、使用本企业医药产品 |
资质 | 医疗卫生人员符合业务需求,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工作经验等客观标准 | / |
合规 | 遵守医疗卫生人员其所在医疗卫生机构的规定 | |
费用 | 费用标准以项目规模、服务时长、专业程度等客观条件为依据,并参照有关规定的标准或者市场公允价格 | |
频率 | 合理限定医疗卫生人员提供服务次数、总金额 | |
支付 | 银行转账 | 避免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方式 |
四、学术推广及讲课费的执法关注要点
对于如何区分“合理、正常”的报酬给付与商业贿赂,实践中传统审查尺度主要聚焦于医药企业在主观上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和《药品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获得不正当商业利益”之目的。结合此前处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我们倾向于认为,执法机关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判断:真实性、合理性以及必要性,这与《指引》内容也是相符合的。
1. 真实性
真实性标准的打击对象系虚构全部或部分学术会议,向特定参会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给付“劳务、讲课费用”的行为。在我们处理类似执法调查案件的过程中,真实性是执法部门关注的最基本的要求,通过虚假会议支付讲课费、劳务费,所体现的商业贿赂主观目的非常直观。
在实操中,我们注意到,执法部门关注相关会议是否只是进行了摆拍、是否涉及编造会议资料、会议图片参会人员着装是否符合实际、参会人员与签到表是否一致。
2. 合理性
合理性标准的打击对象系报酬费用远超其必要商业价值范畴的行为,如讲课内容简单却给付高昂讲课费,课件非由讲者准备和制作等。
我们注意到在此前的执法调查中,某地执法部门进行行政处罚的理由之一就是讲者多次重复使用由某医药企业制作的同一课件8。从此案例中可见,讲者自行制作课件,主要凸显讲者的劳务付出,避免被认定为纯粹的推销药品目的。
3. 必要性
必要性的打击对象系丧失学术价值的学术活动,如学术信息过于基础、陈旧、重复,对于专业人士而言,不具有交流价值等。
我们注意到,某地执法部门重点关注讲者的课件内容。如果课件主要是推介当事人销售的药品,比如该药品与其他竞品的优势,将可能被认为实质上只是为了推销某特定企业的药品,而非具有学术推广的意义和价值9。
此外,在实操中,为规避行政监管,不少医药企业选择与CSO签订服务协议,由CSO举办、开展学术会议,但根据执法实践,只要上游医药企业提供了资金,且对合作CSO的违法行为“明知且默认”,CSO的法律责任就能够穿透至上游医药企业,故在上述情形下,通过CSO构建防火墙并不能规避上游医药企业的法律风险。
比如,我们曾碰到在实务中,部分医药企业选择与学会或者基金会合作,由这些学会或者基金会向医生支付劳务费,比如邀请医生参加征文活动、病例征集后向其支付相应劳务报酬等。我们从执法实践中看到,类似活动背后依然存在医药企业与医院或医生之间“利益输送”的空间,这便触及到了“商业贿赂”的红线,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风险。该些活动无论通过基金会、国内组织或CSO的形式组织发起,其本质内核仍为医药企业与具体医生之间的买卖行为,都是执法部门的调查重点。
五、行政处罚的法律后果
目前,《反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均有对药品领域商业贿赂的限制,其在认定商业贿赂构成要件上并无明显区别。
从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来看,部分执法机关选择适用《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我们理解,这两部文件,更专项针对医药企业与医务人员之间的交往,而且相比于《反正当竞争法》,《药品管理法》的处罚幅度更高。其中,前述文件中所涉及的行政处罚后果之一均包括“没收违法所得”10。
对于违法所得的认定,法律层面的规定如下:《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第二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认定违法所得的基本原则是:以当事人违法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扣除当事人直接用于经营活动的适当的合理支出,为违法所得。本办法有特殊规定的除外。”2021年12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案件违法所得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第三条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计算违法所得的基本方式:以当事人因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款项扣除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必需支出,为违法所得。”此外,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违法所得’问题的批复”中提及,“一般情况下,《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的‘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的全部经营收入’”。
尽管有上述法律层面的规定,执法机关在违法所得的执法口径存在差异。我们遇到不少执法机关在调查中引入审计部门,对违法所得进行审计、出具商定报告或审计报告等,但各方对于计算违法所得计算标准还是有所争论。比如,在原研药领域,部分执法机关认可研发费用作为成本进行扣除,但是对于研发费用范围(失败的全部研发投入是否应分摊入获得成功上市的药品项目)、如何分摊(涉及专利期等)均存在不一样的理解,也直接导致违法所得的审计结果存在差异。甚至出现企业全面亏损情况下,却被处以没收高额违法所得的情形。
此外,实操中,尽管部分医药企业被监管机关查出的违法支出相对较少,但可能面临监管机关一刀切的执法方式,即将某个时间段整体销量作为违法所得计算基础,甚至以提供不当利益后至立案调查期间的全部销量作为计算违法所得的基础。比如,在一些行政处罚结果中,部分医药企业被认定向医生支付讲课费、劳务费仅有小几十万金额,但被没收的违法所得有高达上千万。因此,因果关系也是企业与行政机关博弈的另一要点,即所谓违法行为真实存在情形下,有多少违法行为、导致多大的违法所得。毕竟很多药品已经进入医保名录,将医生(特别是非收取劳务费的医生)的开药数量,均作为其收取不正当利益的结果,逻辑难以自洽。
六、总结
在过去的2024年,国家继续保持对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监管的高压态势,通过更为严格的政策和监管措施,进一步推动医药行业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在这场全面而深入的反腐行动中,医药企业不仅要严格遵循国家政策和法规的要求,更需自觉提升自身合规管理能力,杜绝各类可能引发法律风险的行为。
随着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包括《指引》的实施,企业面临的合规挑战也日益复杂化。跟随着执法机关趋紧的执法尺度,企业需要主动调整业务模式,制定符合新形势要求的合规策略,建立起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此外,医药企业与医疗机构、医生之间的合作形式也需更加透明和规范,避免任何可能被认定为商业贿赂的行为。
我们也在持续关注并参与相关执法案件,亦将在未来就这些案件中执法机关的调查尺度分享更多观察心得。
[1] https://mp.weixin.qq.com/s/CarZpchAk-iFy86nCZfwdA
[2]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5/content_6953851.htm
[3] https://scjg.hubei.gov.cn/zfxxgk/zcwj/qtwj/202404/t20240416_5160439.shtml
[4] https://scjgj.cq.gov.cn/zfxxgk_225/gsgg/qtgg/202407/t20240712_13368199.html
[5]https://www.shanghai.gov.cn/nw4411/20241119/99f9043071744d4aacf48199ba778c1e.html
[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5334164860895194&wfr=spider&for=pc
[7] https://new.qq.com/rain/a/20240708A06VWZ00
[8] 同注6。
[9] 同注7。
[10]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74条: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的派出机构,有权作出《药品管理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药品管理法》第141条: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给予、收受回扣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或者代理人给予使用其药品的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药品采购人员、医师、药师等有关人员财物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三十万元以上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营业执照,并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在
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中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终身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